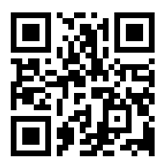过度医疗背后的无知与无奈
日前,齐齐哈尔市又爆出一起“杀医案”,该市北钢医院的一位医生,在出诊时被病人打死。这一惨剧的发生,与之前的“温岭杀医案”,只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,更加一致的是,被杀者都是五官科医生。 到目前为止的多起伤医、杀医案中,五官科医生受害的比例相当大。由此,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浮出水面:“空鼻症”,一个耳熟能详的现象也再次被提起:“过度医疗”。虽然尚且不知齐齐哈尔的这起杀医案的病人,是否有着这种疾病,但“过度医疗”显然是杀医案的又一深层根源,而“空鼻症”不过是“过度医疗”的一个极致而已。 空鼻症 典型的“过度医疗”案例 “空鼻症”是一个疾病的病名,也是对鼻腔状态的形容,因为这些因为鼻塞等难耐症状去就医的人,在检查中发现,鼻腔已经被治疗得很宽大,呼吸时应该没有任何障碍,包括CT检查也“未见异常”。但是,咽喉干燥或有异物感、鼻塞、头晕、睡眠质量差、胸闷、心情沮丧等,原本就医前就有的症状,却毫无减轻,这些人一般都是因为过敏性鼻炎、肥厚性鼻炎或鼻竇炎而做过“鼻甲修除手术”的,误以为导致呼吸障碍的鼻甲,早就被修除掉了,但症状为何依旧甚至加重了? 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说明病人的痛苦:鼻腔有过滤灰尘、加温空气,增加空气湿度的功能,一旦鼻腔过度通畅,上述功能丧失,空气毫无阻拦地进入鼻腔,娇嫩的鼻黏膜直接承受外界刺激,就形成了“空鼻症候群”,而这个问题,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才被国外医生提出的。 五官科 为何成“高危”科室 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明朗,国外的研究表明:具有破坏性的鼻甲手术,开展得越多,病人的投诉也就越多。这一点,同样被国内医生们意识到,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,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等医院的医生,早就在呼吁“对于任何鼻腔疾患,应首先采用规范的保守治疗方式,坚决杜绝任何无限度地扩大鼻腔容积的手术”。 在中国,鼻炎患者人数众多,特别是空气污染加剧之后,鼻炎更成了虽不致命,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常见病,鼻甲手术这种用力多度的治疗,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。因为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中,青壮年男性占了大多数,很可能是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特点,促成了五官科伤医案的发生率要比其他科室要高一些。 “空鼻症”不过是“过度医疗”的一个例子,其他“过度医疗”的当事人则多是选择沉默,他们之所以能认命,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很多“过度医疗”本身就是在病人自己的要求下实施的。 病人为何放弃康复机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是中医肿瘤专家,他在其博客中,不止一次惋惜地提到那些功败垂成的病例:“5个多月前,我去北京,301医院的一位领导,转过多层关系找到我,介绍了一位间皮瘤患者,已经化疗多次,出现腹水、胸水,肝肾功能严重损伤,处于濒危边缘。我是在机场贵宾厅给她看的病,当时我就明确建议,千万别再化疗了,一则化疗对间皮瘤无效;二则她的机体已经不可能耐受,有生命危险,当时她和先生满口答应。治疗一段时间后,她先生发短信给我,说情况大有改善,能够自主活动,胸水明显减少,肝肾功能接近正常,很是感激。 但不久助手告诉我,这个病人走了!我很意外,原来由于康复得还可以,夫妇俩一商量,觉得再做一次化疗更保险,又主动找到医院,要求再做化疗。医生开始不太乐意,觉得会有风险,但是拗不过家属,只好上了化疗,剂量不大,但当晚就呕吐不止,两三天后撒手而去! “输液大国”的赌徒心理 “约七八年前,我的好友,一位资深医学专家,得了胰腺癌,术后复发,找到我,用中西医结合治疗,康复得很好,之后一直稳定多年。他的朋友都是医学专家,为他庆贺七十寿辰时,建议他趁身体状态可以,再补做一、二次化疗,预防预防,有好处,没大碍!并利用工作便利,很快给他安排了住院及特需病房。他咨询到我,我极力反对,他犹豫之后说:都是老朋友、老同事了,好意难却!就做一次吧!结果,进医院当天下午上化疗,当晚发烧,诊断是化疗诱发的胆道感染,而且一烧就是两个多月,70岁的人了,很快就骨瘦如柴,我去看他,他拉着我的手后悔不已。住院两个多月后复查,发现局部有新的变化,3个月后确定新的转移灶,5个多月后人就走了……” 何裕民把这些对主动要求“过度医疗”的病人心理归结为“赌徒心理”,“他们认为,化疗药都是高级药,都是进口药,只要花得起钱,多做一次就多一分保险!这种心理,不独癌症病人,几乎是‘中国式病人’的普遍特点”。 “输液森林”谁来控制 今年2月8日,深圳儿童医院的医生被病孩家长殴打,原因就是医生不让孩子输液。对此,医生解释说,孩子是病毒感染,周期大概为一周,更适合用口服药改善症状。但这个符合病毒感染治疗常规的解释,家长却不能理解,认为是医生对孩子的敷衍,于是,突然将处方甩到医生脸上,医生站起来指责,被一拳挥在脸上。 每年感冒高发季,各医院的急诊室都会竖起“输液森林”,原因之一是病人觉得这样直接打进血管的药物,起效快,力量大,医生又何乐不为呢?一是不违背病人意愿,免去了纠纷矛盾,二是输液总比口服药物利润高,“你再解释,病人也不信,索性依他们好了”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,在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,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,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,远远高于国际上2.5至3.3瓶的水平统计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,结果显示,78.7%的受访者表示,是“病人本身热衷输液治疗”,64.3%的人认为,是“医生为追逐提成收入”,总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 心脏支架中国人比美国人用得多 根据统计,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(支架手术就是介入手术)的数量是2万例,到2011年居然达到了40.8万例,增长了20多倍,需要做支架的人真的这么多吗?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胡大一教授是业内知名专家,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,他很早就炮轰过中国心脏病的治疗问题:中国已经是“心脏支架大国”,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:1到8:1,在中国则高达15:1。在欧洲,稳定性冠心病的病人,做支架的只有4成多,中国却接近8成。 一位医疗器械销售代理透露说,“像关节、支架,说是3万块钱,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1.5万或1.6万,我拿出5000块钱来回馈给你,这5000块钱的一般分成是这样的:设备科是一块,大头还是底下科室,主任拿一部分,然后是上手术的医生。” 贵的支架未必更好 医生也是凡人,他们当初不过是考上了医学院校的普通年轻人而已,从学习到从业,并没有额外的培训或者投入,从本质上保证他们比其他行业更清廉,这种顺手拈来,又只是擦边儿的钱,自然没有不挣的道理。 即便是确定心脏需要做支架,另一个问题又摆在病人家属面前了,医生会问:“是装价钱便宜的还是贵的?” 现在常用心脏支架有两种,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,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。对很多冠心病人来说,这两种支架在疗效和远期预后上区别不大,只能说是各有利弊,不同人群、不同病情应选择不同的支架,也就是说,并不是越贵的就越适合你。 但是,根据统计,我国2009年有约24万人接受心脏支架手术,其中96%的人选择了药物支架,也就是最贵的一种,只有4%的人选择了便宜的那种,而在美国,每年接受此类手术的人超过百万,使用便宜的那种的比例为20%至30%,德国和瑞典为50%。 超越“中国式病人”的盲区 为什么并不富裕的中国人,会选择高价的支架?仍旧是“赌徒心理”,病人首先认为:“便宜没好货”,这个商品通则被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们,毫不迟疑地照搬到了医疗中,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实情,医生是不会为病人拿主意的,因为拿主意就意味着担风险,一旦出问题,医生就有了责任,在现在的医患关系状况下,医生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地说实话,几乎不可能。 于是,医学博士陈作兵就成了一个难得的范例。 陈作兵是浙一医院急诊专家,他78岁的父亲患恶性肿瘤晚期,已经全身转移,无法手术。他将病情如实告知父亲,并把父亲送回诸暨老家,并尊重父亲意愿,不作放疗、化疗,临终之际不做任何抢救措施,只适当镇静安眠,让老人安详离世。 因为陈作兵知道,在英国,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,面临绝症,不再做痛苦但过度的治疗……做到这一点,不仅要抗住没有孝心这种传统压力,还要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帮助他做出理性的选择,而后者几乎是所有“中国式病人”的盲区。 “四分钱处方”的医生无法生存 今年年初,郑州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,因为开出了四分钱的处方被大家关注。这件事缘起于一个浑身红疹的孩子,在到处寻医问药未果之时,找到这位医生,医生问清病情后开出了“扑尔敏”,只需要花四分钱,结果吃药一个小时后,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。 在大处方泛滥的现在,这个4分钱的处方很快被赞誉为“良心药方”。记者为此回访这位医生时,医生很不以为然,因为这样的处方她常常开。 这样的病人其实很多,很多人可能是从胸透,甚至CT开始查起的,花费可想而知,但这种从误诊到确诊的过程,却在客观上成全了医院的生存。而能开出这样良心处方,首先需要正确诊断,否则,药方虽然便宜,一旦贻误病情,之后还会花更多的钱,而能达到如此诊疗水平,需要医生多年的扎实功底和临床积累,如果这样从成本上算,这个处方的价值哪里是四分钱的事?在诊疗费低,药费高的现在,这样的良心处方根本无法体现她的职业价值,而她也很难凭借这种职业良心在现实中生存。 过度医疗与管理制度相关 四川有个“走廊医生”,之所以落魄到只能坐在走廊里,是因为她不能接受医院为了创收而要求她给出虚假诊断,借此把病人骗进医院,花钱治病,因此她被各个科室拒绝,只能在医院走廊上班。“走廊医生”遇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医院都有,之所以“走廊医生”并不多,更多的医生对医院的这一创收手段心照不宣,一个是因为个人的正义感和勇气,另一个就是医生也理解医院的生存难度。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说:“‘过度医疗’存在的那个核心的一个因素,是我们的体制,我们现在的医院,虽然名义上是公立的,但它实际上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,作为医院的一分子,医生也就要通过他的服务量来获得他的收入。”
医生们也觉得很无奈 虽然相关部门多次提出要调整医生的诊疗费,但到目前为止,我国医生的诊疗收费仍旧是很低的,就算是专家号,最高也只是300元,像这种能开出四分钱处方的医生,可能还没有资格挂这个价格号,他们水平再高,也很难通过现有的诊疗技术体现出来,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历了5年本科,3年硕士,2年博士,终于拿到了行医执照的医学生,最终却改行、跳槽的原因。 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专家无奈地说,按照过去医疗的规定,随着病情的康复进程,一般是输液治疗之后改肌肉注射,之后再改为口服,药量要借此一点点减下来,只有完成了这样的治疗顺序,病情才可以稳定,病人才可以出院。但是现在,基本上是拔了输液针头就马上出院了,为什么?“要么是没治疗彻底,要么是根本就没输液的必要,而这两个原因,都和医院的收入有关,因为输液比口服药的利润高,所以可输可不输的都输液了,其次,医院要靠病床周转挣钱,哪有时间让你躺在病床上吃口服药?可不是拔输液针就赶紧出院嘛”。
医生们也觉得很无奈 虽然相关部门多次提出要调整医生的诊疗费,但到目前为止,我国医生的诊疗收费仍旧是很低的,就算是专家号,最高也只是300元,像这种能开出四分钱处方的医生,可能还没有资格挂这个价格号,他们水平再高,也很难通过现有的诊疗技术体现出来,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历了5年本科,3年硕士,2年博士,终于拿到了行医执照的医学生,最终却改行、跳槽的原因。 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专家无奈地说,按照过去医疗的规定,随着病情的康复进程,一般是输液治疗之后改肌肉注射,之后再改为口服,药量要借此一点点减下来,只有完成了这样的治疗顺序,病情才可以稳定,病人才可以出院。但是现在,基本上是拔了输液针头就马上出院了,为什么?“要么是没治疗彻底,要么是根本就没输液的必要,而这两个原因,都和医院的收入有关,因为输液比口服药的利润高,所以可输可不输的都输液了,其次,医院要靠病床周转挣钱,哪有时间让你躺在病床上吃口服药?可不是拔输液针就赶紧出院嘛”。
诊疗方案其他内容
杭州三甲医院
手机扫码使用医院网